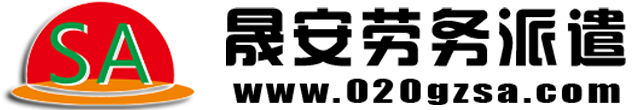國家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的發(fā)展進(jìn)程,體現(xiàn)為由單一的行政治理,走向行政治理與社會治理協(xié)同發(fā)展有機(jī)統(tǒng)一的自然演進(jìn)歷程。當(dāng)代中國社會治理的任務(wù)是: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,以促進(jìn)社會公平正義;通過深化社會體制改革,完善收入分配制度,以促進(jìn)全民共享改革成果、實(shí)現(xiàn)共同富裕;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的精準(zhǔn)識別、精準(zhǔn)幫扶、精準(zhǔn)管理和精準(zhǔn)考核,引導(dǎo)各類扶貧資源優(yōu)化配置,以實(shí)現(xiàn)扶貧到村到戶,構(gòu)建精準(zhǔn)扶貧長效機(jī)制,為科學(xué)扶貧、精準(zhǔn)脫貧奠定堅(jiān)實(shí)基礎(chǔ)。將精準(zhǔn)扶貧納入國家治理能力建設(shè)的社會治理之中,不僅對扶貧實(shí)踐具有制度指導(dǎo)的價值意義,而且是扶貧政策在對象群體確定和實(shí)現(xiàn)目標(biāo)政策上的漸進(jìn)完善和精準(zhǔn)化努力。
縱觀中國扶貧治理的發(fā)展歷程,經(jīng)由“救濟(jì)式扶貧治理”“開發(fā)式扶貧治理”“參與式扶貧治理”的歷史演進(jìn)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肇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“救濟(jì)式扶貧”,以解決貧困群體的物質(zhì)貧困為目標(biāo),其治理機(jī)制重在從物質(zhì)援助的制度輸入上,對貧困群體實(shí)施確保其基本生活的經(jīng)濟(jì)救濟(jì)。然而,由于貧困的形成,不只是表征為經(jīng)濟(jì)生活的物質(zhì)貧困,還包括無法獲得最低需要的能力貧困和區(qū)域資源供給乏力的有用性貧困。因而,從確保貧困人口能力素質(zhì)再生產(chǎn)和提升區(qū)域資源供給質(zhì)量的治理視角,自20世紀(jì)90年代開始,我國政府將扶貧治理模式的適時創(chuàng)新定位為:以區(qū)域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為基礎(chǔ),人力資本投資為主導(dǎo)的開發(fā)式扶貧模式;以社會再分配為基礎(chǔ),產(chǎn)業(yè)開發(fā)為主導(dǎo)的參與式扶貧模式。其治理模式變遷的價值彰顯,體現(xiàn)為從個體能力和區(qū)域貧困的經(jīng)濟(jì)視角,將外在的物質(zhì)輸入治理,轉(zhuǎn)化為內(nèi)在的能力開發(fā)治理,包括貧困人口的能力開發(fā)和貧困區(qū)域的資源開發(fā)。正是經(jīng)由三大扶貧治理模式的歷史演進(jìn)和制度安排,使得7億多農(nóng)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,貧困發(fā)生率從20世紀(jì)80年代的80%以上,下降到2014年的7.2%。
進(jìn)入新世紀(jì)以來,當(dāng)經(jīng)濟(jì)與社會的協(xié)調(diào)發(fā)展,漸次取代單一的經(jīng)濟(jì)增長目標(biāo)時,人們對于貧困內(nèi)涵的認(rèn)識,也從個體主義的經(jīng)濟(jì)貧困、能力貧困拓展到社會結(jié)構(gòu)層面的權(quán)利貧困領(lǐng)域。關(guān)于扶貧治理工具的政策選擇,亦轉(zhuǎn)移為以政府為主導(dǎo),通過公共財政的再分配功能,改變社會結(jié)構(gòu)對貧困人口發(fā)展的制約因素,促進(jìn)人們選擇環(huán)境的改善和提供均等的發(fā)展機(jī)會,以確保窮人的權(quán)利平等。這一認(rèn)識水平的提升,表明人類關(guān)于貧困的認(rèn)知標(biāo)準(zhǔn),正由“個體主義”的經(jīng)濟(jì)、能力、資源貧困,轉(zhuǎn)向從社會體制的歷史變遷之中解決“缺少發(fā)展能力、促進(jìn)權(quán)利均等和構(gòu)建城鄉(xiāng)融入”的結(jié)構(gòu)性貧困。它同時也表明,關(guān)于扶貧治理模式的創(chuàng)新,已從單一的經(jīng)濟(jì)治理領(lǐng)域,擴(kuò)展到更為豐富的社會治理領(lǐng)域。以社會治理實(shí)現(xiàn)精準(zhǔn)扶貧目標(biāo),成為轉(zhuǎn)型中國促進(jìn)權(quán)利均等與社會公平、提升民生質(zhì)量、實(shí)現(xiàn)最后7000萬貧困群體徹底脫貧的必經(jīng)路徑。
第一,在社會治理中,實(shí)現(xiàn)精準(zhǔn)扶貧目標(biāo),體現(xiàn)了扶貧治理結(jié)構(gòu)是物質(zhì)救濟(jì)與制度保障的有機(jī)統(tǒng)一。既有的扶貧模式,從以經(jīng)濟(jì)增長促進(jìn)物質(zhì)財富總量增長的視角,經(jīng)由資金資本注入和人力資本提升的雙重驅(qū)動,整合貧困地區(qū)的區(qū)域資源和區(qū)位比較優(yōu)勢,以實(shí)現(xiàn)貧困人口和貧困區(qū)域的雙重脫貧。但是,由于缺乏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套介入,致使少數(shù)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口和因病致貧的家庭,陷入貧困累積的“因果循環(huán)”之中。社會治理取向的精準(zhǔn)扶貧,在強(qiáng)調(diào)以物質(zhì)財富的增量解決貧困“面”的普適性問題的同時,亦強(qiáng)調(diào)以社會保障制度,去精準(zhǔn)兜底“點(diǎn)”上的貧困人口,確保到2020年穩(wěn)定實(shí)現(xiàn)所有農(nóng)村貧困人口不愁吃、不愁穿,農(nóng)村貧困人口享有義務(wù)教育、基本醫(yī)療和住房安全保障。
第二,在社會治理中,實(shí)現(xiàn)精準(zhǔn)扶貧目標(biāo),體現(xiàn)了扶貧治理主體是黨的領(lǐng)導(dǎo)與多元參與的有機(jī)統(tǒng)一。既有的扶貧模式,以行政一元救濟(jì)的科層制管理為主體,以資金投入、技術(shù)輸入和人力資本提升作為制度化工具,通過“自上而下”的政策落實(shí)和社會動員,解決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。行政治理中單一化主體的“任務(wù)型”推進(jìn),決定其精準(zhǔn)識別的模糊性和精準(zhǔn)管理的有限性;社會治理取向的精準(zhǔn)扶貧,將關(guān)注民生和強(qiáng)化貧困區(qū)域的公共服務(wù)功能合為一體,將貧困人口“需求表達(dá)——利益滿足——公共服務(wù)供給”融入“黨委領(lǐng)導(dǎo)、政府主導(dǎo)、社會協(xié)同”的治理框架之中。其中,黨委領(lǐng)導(dǎo)表征為整合多元社會力量,凝練精準(zhǔn)扶貧共識,提升精準(zhǔn)扶貧責(zé)任;政府主導(dǎo)表征為合理配置扶貧資金、資源和人力,提高扶貧滿意度;社會協(xié)同表征為,通過社會多元主體的協(xié)同參與,增進(jìn)扶貧治理的開放性,從而形成集扶貧治理和區(qū)域發(fā)展為一體的黨和政府與社會和諧統(tǒng)一的互動渠道。這一通道不僅為黨的基層組織直接嵌入扶貧事務(wù)之中,構(gòu)建了實(shí)踐性支撐,而且為基層黨組織向貧困社區(qū)的制度化融入,提供了合法性依據(jù);既增進(jìn)了黨執(zhí)政的社會性質(zhì)和意義,又確保了扶貧質(zhì)量的穩(wěn)定性和可持續(xù)性。
第三,在社會治理中,實(shí)現(xiàn)精準(zhǔn)扶貧目標(biāo),體現(xiàn)了扶貧治理對象是權(quán)利自救與奉獻(xiàn)社會的有機(jī)統(tǒng)一。既有的扶貧模式,將扶貧治理對象作為被動的游離于社會之外的“可憐人”,是政府和社會必須施予幫助的“弱勢群體”。因而,在幫扶貧困群體的同時,也將之置于正常的社會關(guān)系和社會結(jié)構(gòu)之外,產(chǎn)生無形的“社會排斥”現(xiàn)象。社會治理取向的精準(zhǔn)扶貧,不僅呼吁高質(zhì)量的、以構(gòu)建社會融入為目標(biāo)的扶貧工作機(jī)制,而且強(qiáng)調(diào)對扶貧對象實(shí)施集體認(rèn)同和自我價值實(shí)現(xiàn)的現(xiàn)代培育。窮人不僅追求自身生存與發(fā)展的權(quán)利,而且也是社會整體的一分子。在提升自身生存能力的同時,也能平等奉獻(xiàn)社會,增進(jìn)公共利益。
廣東晟安勞務(wù)派遣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(yè)的人力資源服務(wù)公司,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,專業(yè)從事勞務(wù)派遣、人力外包、代理招聘、社保代
理等等業(yè)務(wù),為事業(yè)單位提供專業(yè)的個性化第三方人力資源全面解決方案。
以上是小編整理相關(guān)內(nèi)容,希望能幫助到大家。各位想了解更多關(guān)于廣州社保方面知識可以咨詢【廣州晟安勞務(wù)派遣公司】。
聯(lián)系方式:020-38674898